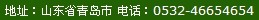|
[加拿大]贾尼丝·格罗斯·斯坦著 杨晋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时至今日,效率被奉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标,公民对其痴迷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效率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追求效率?国际关系学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通过与公民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教育和全民医保两个窗口,披露各个领域对效率滥用的现象;并指出了在国民安全的重大课题面前,公众和政府的责任。 效率崇拜 对效率的需求比比皆是。在我们的私人生活里,公共生活中,富贵阶层,赤贫社区,要求效率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确保我不是在想象中处处听到或读到“效率”二字,我装备了一台崭新的——高效的——电脑,里面配备了一个更高效的全新搜索引擎,借此我在众多广受尊敬的已出版文献里搜索“效率”这个词。 年关于效率的索引有条,到了年,已经超过5.5万条。由此看来,在过去10年里关于效率的写作增长了近%!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曾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评估该省高中后阶段教育机构的行政运营情况。最近出台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该省的大学是加拿大大学中行政运营开支最少的。此报告认为,安大略的大学总的来说是高效率的。在哪些方面高效呢?我很纳闷。它没有就这些大学提供的教育质量给出数据,也并未发问,与行政成本相比,大学给予学生的教育该有多好,才能让安大略的学生——以及公民——得出成本效益高的认知?它并未发问,在哪些方面高效?为了谁而高效?它只看重低廉的核心行政成本,以其为固有目的,并将其定义为效率。 这种把效率视作本身固有目的的痴迷并不限于局部一隅……挖苦说:“比什么效率?要比福特汽车公司效率高吗?还是要比日本交通部效率高?”在不同的人类活动圈效率显然会有不同的含义,衡量的标准是相对的,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效率的话语不仅渗透了私有的和非营利的区域,也进入了公共部门。我们越发把自己视作“消费者”,我们的领袖们和我们的公共机构亦如此看待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期望政府和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能高效到位,期望我们的“付出能有回报”——付出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同样期望——就好比市场条件下的消费者一样——能对享受到的服务表示满意。市场的话语已逐渐延展至公共领域。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认为,公民参与,即公民们聚集在公共空间参与到公共话题里来,是创建“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指的是对信任和互惠的期望,这对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同样,此处的用语让人大开眼界:构建社区所需的密集关系网络成了“资本”,也就是一种可以耗尽或者可以积累,可以高效投资也可以荒废的资源。这样的意象作为公众性情的度量颇有揭示意义:效率语言被用来保卫社会。不知什么缘故,使用市场的语言比使用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语言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果说关于效率的话语随处可见——在私人生活里,在非营利的领域里,在公共生活里,那么作为概念的效率使用的场景则大不相同、内涵迥异。效率并非新的概念,而是可追溯到古代,那时候市场的重要性还无法与国家匹敌。理顺效率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有助于我们抓住那些仍穿插在公共讨论中的线索。我认为至少有三条重要的线索:效率在客观角度下被视为富有生产力的机器,在主观角度下被当作内心的满足,以及在国家无能为力时,市场发挥效率的可能性。我们当前的效率讨论正是由这三条线索编织而成的。 效率的思考:富有生产力的机器 现代效率概念的发端,正逢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兴起和18世纪英格兰商业活跃之时。亚当·斯密(AdamSmith)在观察了工厂里的别针生产过程之后明确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别针的生产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比如剪线、磨尖、拉直等。斯密计算过,如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所有的任务,他一天最多能完成20枚别针。然而如果把这些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工人,工厂里的每个工人平均每天能生产枚别针。斯密揭示了市场和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 市场的存在促成了劳动的分工,其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分工做到非常细致。一个乡下的工匠可以是马车工匠、房屋木匠、广场建筑工或者是一个制橱柜的、雕木头的,每一件这样的活计在城里都可以成为单独的生意。斯密并未担心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会影响集体利益。他著书立说于工业革命早期,非常有信心通过市场的作用,即通过那只隐形的手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和集体利益和谐地统一起来: 我们享用晚餐并非仰仗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善意,而是仰仗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我们应该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nmenzx.com/jmxtq/9937.html |
当前位置: 金门县 >效率middot公平middot
时间:2021/6/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它是斯坦福ldquo死对头rdqu
- 下一篇文章: 抽烟喝酒烫头,全美最丧年轻人在这里起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